小时候我曾有过一段“怪力乱神”的时期,大约在六七岁以前。当时我们一帮毛孩子,总觉得附近山林里藏着神秘莫测的怪物,实在是好奇难耐,可又谁都不敢靠近,整天只能徘徊在四周起哄,一惊一乍,体内像是有春雷在涌动。回想起来,那感觉刺激又甜蜜。
我至今都相信那是一种出自身体、也栖居在身体中的原始想象力。在那个年纪,意识还没有彻底独立出身体而存在,它俩还粘连在一块,所以我大致还处在身心合一的晚期。不过这感觉后来就慢慢消散了,我开始变得理智。
 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很多年后读起《山海经》,有点恍然大悟。里边的山经部分罗列了各种大山,光怪陆离,奇鸟异兽遍布,几乎就是童年时代魂牵梦绕的那个蛮荒世界。那个时期元气淋漓,想象力漫无边际,而那种状态也经常被人们称之为童趣,我想《山海经》诞生的年代,在历史上大致也属于是人类的童真时期。
到了20世纪,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写了本小说叫《看不见的城市》,体例与《山海经》很接近,只是焦点从山林变为了城市,各种城市目不暇接。不过城里已经是主客二分的成人世界,理性与逻辑主导一切,这大概是人类历史上的成年时期。时过境迁,不论从空间还是从时间上来看,我与山林都被重重城市远隔。
但我一直有个愿望,希望能定居在一个下班后很快便能溜进山里的城市。这是我心中宜居城市的重要标准,城小而与山接壤。《论语》中讲,仁者乐山,对我来说,山是一种生活刚需,实现进山自由,是我的执念。
《韩诗外传》对仁者为什么乐山有过解释。它说山之所以被瞻仰,是因为“草木生焉,万物植焉,飞鸟集焉,走兽休焉,四方益取与焉,出云道风,从乎天地之间”,说白了就是此乃大自然之聚集地,热闹得很。
英国散文作家娜恩·谢泼德一生都在苏格兰高地的某处山脉间游荡,并以一生经历写出了《活山》。在书中,她将山的形成归因为“原生力”,这个词接近于古诗里“造化钟神秀”中的造化。她这样描写在山中行走,“一个人可以在各种原生力中穿行,却无法掌控它们,这种和原生力的接触,也唤醒了我自身深处如风雪般深不可测的力量”,她还说在山里时,感到身体在思考。
身体思考,对此我也有点体会。那是很多年前,在山中的一次雨后慢跑。透过水墨晕开般的氤氲雾气,连绵山峦像一只背脊尖峭的甲虫匍匐在我远处,而大朵白云从它脊背一侧喷薄而出,天地间仿佛在呼吸吐纳。那是我长这么大毫无防备的时刻之一,我感到山是活的,千真万确,同时体内还有力量在呼应,像手机感应到了信号极强的Wi-Fi,还没有密码。
卡尔维诺早期还写过一本城市小说《马可瓦尔多》,里边讲了在某个枯燥乏味的城市里,有个人叫马可瓦尔多,此人善于从城市的缝隙里捕捉“草木生焉、万物植焉,飞鸟集焉”的蛛丝马迹,但几乎都以荒诞告终。
比如他发现路边长出野蘑菇,便喜出望外,采摘了很多回家,最后却食物中毒,第二天他又出神欣赏天空中飞过的候鸟,又不慎闯红灯被开了罚单。类似这样的故事日复一日,不断在发生。这是个受困于水泥沥青,但渴望山野的城里人。
在我们身体里,都居住着这样一个半睡半醒的马可瓦尔多。娜恩·谢泼德说,“身体在山里会有一种超脱的快感,像某种取代思维的病症,但所有患者绝不会请求被治愈”。这就叫斯人而有斯疾,虽然大家都是成年人了,但我们还永远牵挂城外的山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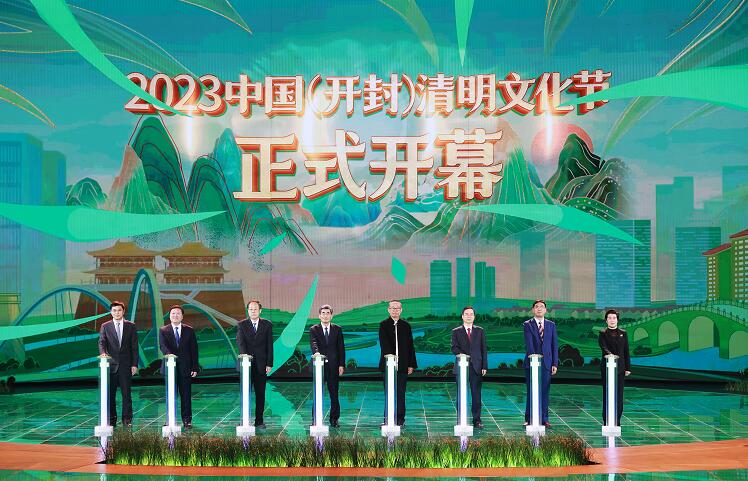 传承文明 拥抱春天 2023中国(开封)清明文化节启动仪式举行
传承文明 拥抱春天 2023中国(开封)清明文化节启动仪式举行
 引金融“活水” 润科创“沃土”
引金融“活水” 润科创“沃土”
 河南省水路运输实现开门红
河南省水路运输实现开门红
 河南自贸试验区累计入驻企业12.3万家
河南自贸试验区累计入驻企业12.3万家
 河南大范围降水+强对流+大风降温来袭!注意防范
河南大范围降水+强对流+大风降温来袭!注意防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