 (相关资料图)
(相关资料图)
在预订了人生中最重要的演唱会——Wembley体育场演出后不久,Damon Albarn(译者:乐队主唱,金牙,牙爹)向他的Blur乐队成员播放了一些有可能成为乐队重聚新专辑的demo。这是一次轻松的推销:《The Ballad of Darren(达伦的情歌)》将成为他们九张专辑中最美丽、最紧凑的一张,优雅地编排了浓郁的和声、巴洛克风格的华彩和一连串90年代的角色扮演。他们在早期的重聚演出中以新歌《St. Charles Square》开场,这首歌就像迈入了会议室,用无法抗拒的方式敲打着白板:这就是你真正记得的Blur,以他们所有狂热的荣耀。
你可能会一遍又一遍地强迫自己播放《St. Charles Square》——一首带有回味往昔的“Oiiii!(译者:请听Parklife)”和滑动指板的怀旧蓝调斗争者——也许还在等待一个恰当的副歌,但非常高兴他们回来了,Blur就是Blur。除了Pulp的最新重聚演出外,Blur的两场售空的Wembley体育场演出也受到评论家的好评,这些评论家在90年代的音乐媒体的鼎盛时期走红。不管好坏,Britpop和Blur又回到了议程上。
Blur因对平庸英国生活进行了编码式的描述而同时受到尊崇和反感,这在90年代初得到了永久的传世。来自Essex中产阶级的男孩Albarn以如此频繁的节奏发表他的评论,以至于有时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带有伦敦俚语口音——在嬉皮士年代,他宣称摇滚乐“过于华丽和小圈子”,声称更喜欢“流行音乐的含糊性,没有任何真正的讯息”。兴奋的杂志编辑们搁置了对丛林音乐和鼓打贝斯的报道,将资源投入到这些不关心事务的艺术学院怪人身上,让他们占领排行榜和白天广播。
一切都在1997年改变。戴安娜王妃去世了,Blur开始喜欢上Pavement乐队。新自由主义者Tony Blair执政,开始让左翼的所有人感到疏远,从首先开始就是跟随他进入权力的Cool Britannia艺术家们。记者凯特琳·莫兰发表了一篇嘲讽的专栏文章,宣布“Britpop已死”,然而她上个月仍然在Wembley体育场发布了推文:“哦,Blur,这三十年,你都是最棒的。”幸存下来的Blur——他们从Britpop的低谷中艰难地爬出来——是90年代漫长时期的象征:这个十年凝固了伦敦媒体阶层的文化和政治想象。
Albarn现在已经完成了从名人骚扰者到吸毒者再到瑜伽达人的转变。他瞬息万变的面孔掩盖了他作为流行乐界最焦躁不安的人的地位:自从Blur于2015年发布了专辑《The Magic Whip(魔鞭)》以来,他与无限可扩展的Gorillaz乐队一起发布了四张专辑(译者:经典小号比大号红),并与其他项目合作发布了三张专辑;他还创作了《爱丽丝梦游仙境》音乐剧,构思了一部将“歌特与俱乐部音乐”混合的歌剧,并试图为Netflix制作一部Gorillaz电影。他在马里被授予了“Local King”的称号(译者注:牙爹曾与当地音乐家合作专辑Mali Music)。像许多戒毒者一样,他一直在努力摆脱懈怠。Blur的第四幕一直在等待着他。
Damon Albarn表示《The Ballad of Darren》这个标题诙谐地向Blur的保安和普通人Darren “Smoggy” Evans致敬,但也暗示了更多戏剧化的部分。这个隐喻的标题与Albarn的浪漫的一面相吻合,或者至少是他的叙述者。回归单曲《The Narcissist》回顾了Blur的历史,并面对他们的曾经成瘾的遗产:Albarn与Graham Coxon(Blur吉他手,面面)呼应的部分表现出对吉他手自己破坏性酗酒行为的同情。整张专辑中,Albarn描述了乐队在水晶般的沉思中漂流时面对的心碎和化学诱惑,由詹姆斯·福特的双层制作保护着。在击中他们的合唱线索后,《The Narcissist》和尾曲《The Heights》都以吉他噪音高潮,威胁着或者承诺着毁灭。
Albarn表现出袒露心扉,但在他所说的“超越”自传时,他伸展得太远,以至于心肠掉了出来。《Barbaric(野蛮)》——一首懒散的分手颂歌,带有Johnny Marr风格的即兴和有关“野蛮”不和的副歌——实际上是否指涉了政治分歧?这些心碎的歌曲刻意保持合理的否认性。Albarn援引时事,绕过富人的自怜,好像被虚假的攻击文章所困扰:“五十岁重聚,Blur从房主的角度重写《Country House》,”等等。
当他讲故事时,他邀请我们一起进入他的故事区:我们看到《St. Charles Square》中的“basement flat with window bars(带窗栏的地下室公寓)”,听到《Russian Strings》中的“balalaikas and singing”(阿尔本说这是一首关于普京“老朽独(自)裁(剪)”的歌)。亮点《The Ballad》将分手与死亡联系起来,伴着《Think Tank》上的抗抑郁曲调。但在《The Everglades》等美丽的歌曲中,如此自豪地写下自己的歌词的Albarn只能召唤出模糊的“paths I wish I’d taken”和“times I thought I’d break”。这些陈词滥调中有一种讽刺,鼓手Dave Rowntree在今年1月承认:“我们在20多岁时写的嘲笑老年人的歌现在指向了我们自己……我记得当时想,这些人什么都不懂。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还活着!”(译者注:不愧是领导)
《End of a Century》等讽刺性的颂歌总是充满着潜在的恐惧,因为我们可能最终会成为它们那些土气、家庭化的主题(译者注:所谓过去的子弹打中了现在的自己)。对于一些人来说,团聚的夸大其词背叛了这些歌曲的持久刺痛——一种坚硬的焦虑,认为事情只会变得更糟,生活在那些日子里达到了巅峰。《The Ballad of Darren》将这种忧郁与中年动荡联系在一起,但它的温和和简明取代了Blur的特点,那些将更有力地唤起一个人的崩溃:Coxon的陷阱掉落、钝利的尖声和闪亮的蓝调;Albarn的激流游入迷糊又怪异的流派。Albarn扮演着心碎者的角色,但这些精心打磨的歌曲召唤出的不只是痛苦,更多的是失落的感觉,中年衰退的温暖氛围,以及随着岁月推进逐渐消失的信念,不再相信危机总是能揭开你人生下一章的帷幕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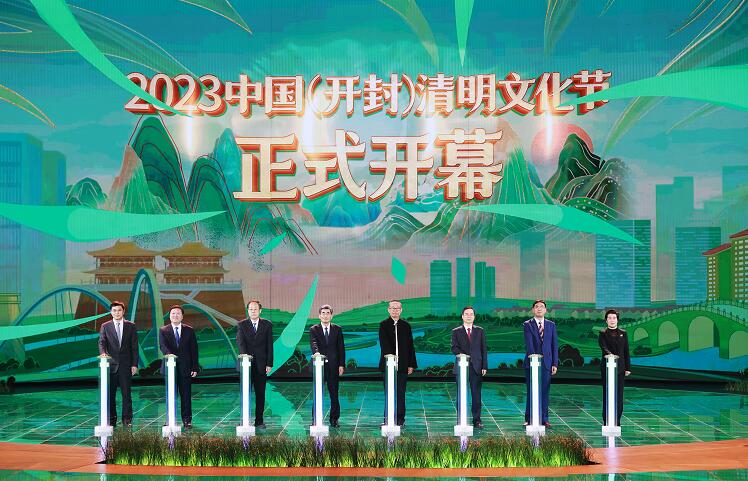 传承文明 拥抱春天 2023中国(开封)清明文化节启动仪式举行
传承文明 拥抱春天 2023中国(开封)清明文化节启动仪式举行
 引金融“活水” 润科创“沃土”
引金融“活水” 润科创“沃土”
 河南省水路运输实现开门红
河南省水路运输实现开门红
 河南自贸试验区累计入驻企业12.3万家
河南自贸试验区累计入驻企业12.3万家
 河南大范围降水+强对流+大风降温来袭!注意防范
河南大范围降水+强对流+大风降温来袭!注意防范